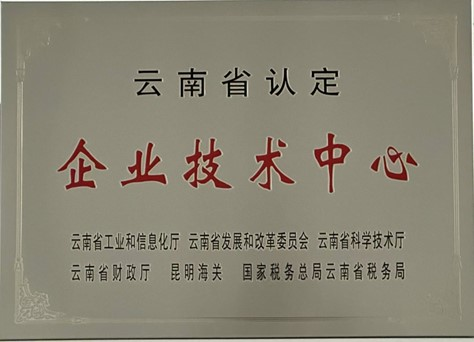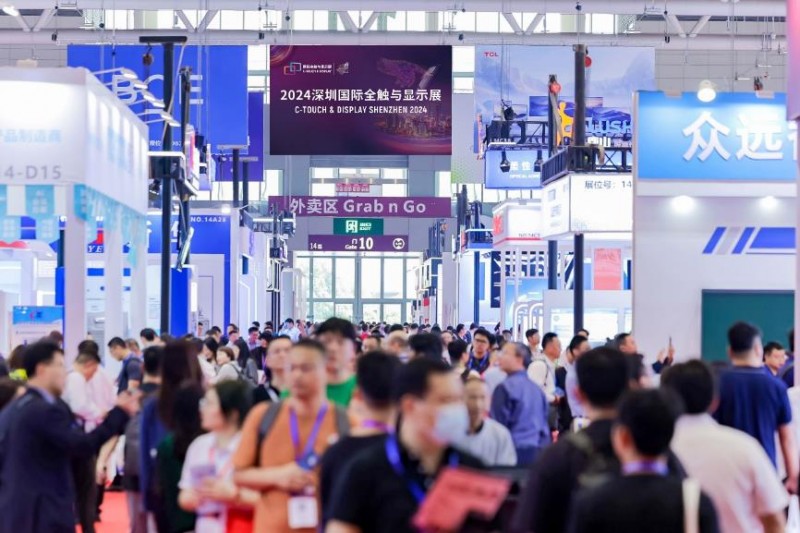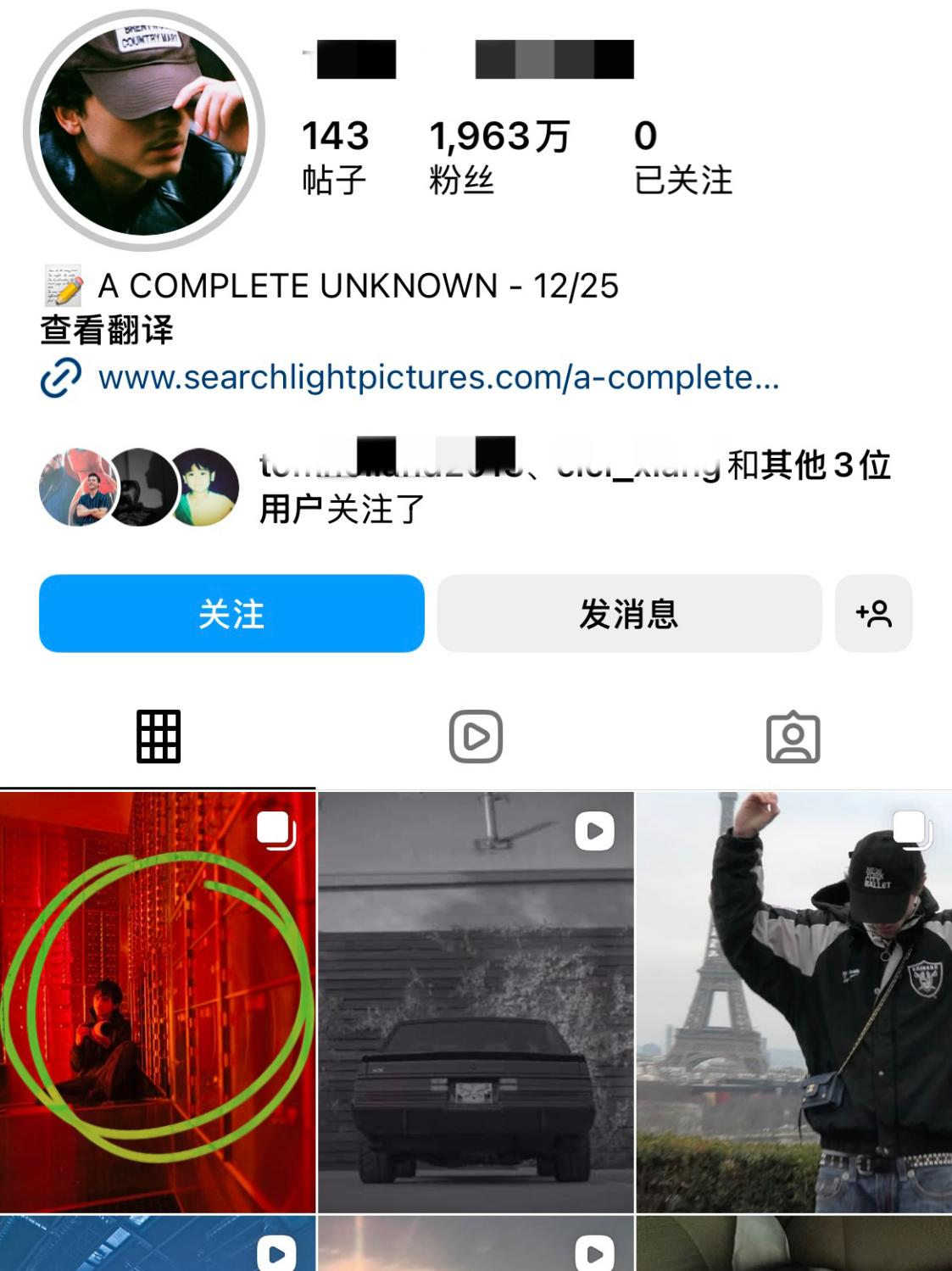我在道布呼都格火车站当“电工”
旅行家专栏 > 吉青子的专栏 > 我在道布呼都格火车站当“电工”
我在道布呼都格火车站当“电工”
By 吉青子 2019-01-23
马蜂窝旅行家专栏出品 | 已有3059人阅读
其实道布呼都格站的全称是道布音呼都格站,只是锡盟惯常的长地名(当然六个字的地名在锡盟也算不上什么)再加上“站”字,已经超出铁路地名系统字符上限,只好抹去一个字,也使得站牌上的字因此生生从中间断开了一截。
位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道布音呼都嘎苏木的道布音呼都格火车站是锡盟腹地戈壁上的一座铁路职工通勤车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快递也无法到达,离得最近的城市是111公里开外的中蒙边境二连浩特。

那时我已在内蒙独自逗留了两个月。任伟邀我去他们车站体验酷暑戈壁中的天窗作业,他是集通铁路锡林浩特综合维修段的铁路人,平时主要在临近二连浩特的伊拉勒延站,偶尔会调到道布呼都格来。有这样的好机会,当然是要答应的,为此我才有幸来到这个遥望中蒙边境的边陲小站。
抵达道布呼都格站时是正午,戈壁是惯常酷烈的炎热和令人心痛的干旱。任伟在车站等我,我在站台和通行于锡二线、锡通线的列车员乌日根道别。在这个比小站还要小的铁路职工通勤车站,相聚、告别都太过引人注目。除了会令火车上的乘客注目,容纳这些情绪或故事的车站也显得过分寂寥,似乎永远都不会有庞大如北京站那样的窒息感,也没有诸多二三线城市站前的吆喝、汽笛、吵架、行骗的众生相。
任伟要带我去附近的“兄弟车站”敖日格勒站,我问多远,他语气轻松,说:也就七公里。
“能走吗?”他问我。
“能,能……的吧。”
当然不能,太热了。我顶着戈壁烈日,四野无风无人,太阳晒在脸上,热得说话也蔫了。




任伟在荒凉贫瘠的草地上捡石头,他戏谑称之为,一个信号工的无聊闲暇时光。
他提醒我可能会有蛇出没,要小心。
“那你如果看到这些蛇的话,会怕吗?”
“不会啊。这就是被它咬的啊。”他抬起腿,指了指被蛇咬过的疤。
“那万一,万一有毒呢?”
“有毒就死呗。血清在呼市呢,这地方一点儿也没有。”
“那就是等死喽?”
“对。等死。”
他的语气平淡。但也是事实,真的遇到毒蛇、洪涝、灾祸,因孤立无援,即使技术足够,也只能白白受灾甚至死去。一场雨来,任何都很有可能淹在混了泥土的水里。在我离开后的8月,道布呼都格火车站淹在雨水里,车站的一二十名职工,就此搬去了伊拉勒延站,后来的道布呼都格站,仅仅剩下三两人驻守了。
“很正常。看,这就是被它咬的。菜花蛇,无毒的。”
“走吧,带你上线路。”
太热了,累得口干舌燥,只好作罢,尽管我对那座同样的小站充满好奇,此刻也觉得相隔万里,遥不可及了。


“工区晚上吃饺子。”对于北方人而言这么隆重的事情,他还是淡漠地说着。
终于走回车站,他带我参观会议室,并无多少陈列,但设施在整个车站来说已属豪华。有一台电风扇,还有电视可以看。接收频道要不断调整那台被称之为“锅”的接收器,而在这茫茫戈壁草原,能有手机信号已是不易,想要看到丰富的电视节目还是遥远了些。因此我只能在百无聊赖中从一个内蒙卫视调到另一个内蒙卫视,断断续续看着唯一能看的节目86版《西游记》。
车站养了三只乖巧聪明的狗,一只叫“道布”,一只叫“呼都”,还有一只叫“格格”。三只小狗偶尔被带到伊拉勒延换个环境——但又有什么不同啊。
道布最活泼聪明,深得车站职工喜爱。额头上一撮白色的爱心图案,头上竟然还神奇地有中国铁路标志的花纹,也因此车站的人说道布“生是铁路的狗,死是铁路的死狗”。
我们在车站身后的土坡上与厨师大爷大妈聊天,这对老夫妻承包了车站职工们的一日三餐,顺便还经营着一家小卖部。道布和呼都总是从小山坡那头跑过来,一头扎进土里,在尘土里打够滚,再来蹭我的脚,热情地把小爪子搭在我的膝盖上。

任伟带我去他们的生活区。穿过只有一个篮筐的球场,翻过铁围栏,和站内职工们一一打过招呼,便就是他们吃饭娱乐的地方了。简单得几乎没有陈设,一张大圆桌就是社交汇聚地。有的房间紧锁,还有的房间在施工。车站的人用一种奇异的眼神看我,是在诧异到来的是一个女性,还是诧异一个女性的到来。
有一个人看了看我,说:“我见过你。”
“啊?”
“你好面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有一点想笑,还有这样复古的打招呼的方式。
他认真回想,问我:“你是不是之前穿过一件蓝色衣服,背着一个相机?”
我有点惊恐,他是如何知道的。 他又是在哪里见过我的。
我有幸凑了份热闹,在这里吃上了一顿饺子。饺子这种北方节日的图腾,不知车站的人多久能吃上一次,毕竟他们的伙食几乎全来源于大爷大妈,无论是大爷包的饺子,还是大爷卖的零食。
饭后在站台散步,静静地看日落。任伟他们放着惯常从汉人手机里听到的草原歌曲,有人在站台边缘和女友通电话。天色迷离,夏日傍晚的风令人沉醉。一天中最美妙的时光便是此刻:黄昏正浓,因着一望无际,光芒能铺天盖地。视野之内,旷野以外,大地之上,苍穹之下,都是天神赐给的福泽。草原、戈壁、羊群、建筑、铁道还有我们人类,有什么孤独,有什么苦难,在这样极致的黄昏中,都被天色抚慰了,暂时忘却不能忘却的,瓦解不能和解的。



洗漱有多困难?所谓的水房,放出来的水是土黄色的,有浓重的铁锈和土腥味。仅仅几分钟盆底就堆了一层沙尘。唯一略微干净一点的,是在一个简易的小厨房,但也是浑浊的。我简单地抹了把脸,刷牙时嘴里也是沙子。水量有限,毕竟不是自来水,而是职工们用一点人工装置从车站附近引的水。一层楼有两个卫生间,一个男卫生间和另一个男卫生间。我出来时迎面碰到车站里一个小伙子,两个人都非常尴尬,假装没有看见对方。
我问任伟是如何解决洗澡问题的,他说,哦,我一般攒两天去伊拉勒延洗。
站房身后直面沙坡,夜晚的风狂烈,拍打窗户,沙子也会扫进来。我睡前已将床铺收拾一番,醒来枕头上、被子上、鞋子里、脸上到处都是沙子。因为任伟将我独自安置在一层楼,我占了他的宿舍,问他去哪里睡,他嘿嘿一笑:我们睡机房。他领我参观,可能除了站长,车站所有小伙子都在这个大“空调房”里打着地铺吧。横七竖八,闻着对方的汗味睡去。
星星繁密,草原起风,单纯得没有心事,很快便睡去了。
翌日我5点便起了床,赶在他们起床之前洗漱完毕,下楼看见他们大多还在休息,调度室却亮着灯。他们穿着工服,盯着电脑屏幕,对讲机的联控一直未停。仿佛这一夜都没有睡去,或者他们中的人最早来开门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万物还沉睡,草原上那些久远的志怪传说刚刚才安静下来。他们也许一夜难安,早早醒来,在清晨的第一趟火车来临之前,做好联控,做好调度,做好接车准备。
站长看见我,有点惊讶,然后又告诉我,一会儿要来车呢。
不一会儿就听到一辆有节奏的柴油机轰鸣声远远传来,似乎是东风8B,连忙跑到站台外去等,呼啸了一夜的风尚未离开,然而内燃机总是如此性感、销魂,冷冽的晨风中,声势浩大地开来,又牛气轰轰地开走,仿佛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豪气震天。